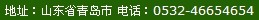|
治白癜风多少钱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525518.html 在角斜场负重伤的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卢福祥(现年91岁)苦苦寻找救命恩人现东台市新街镇沿海村十分头村 年2月16日(正月二十六),18岁的卢福祥在角斜场(靠近原旧场村)身受重伤昏迷,差点被埋葬,万幸得到十分头一家三位妇女的救助。她们是 赵氏40多岁(人称冯嫂), 儿媳王秀英21岁(人称喜子家的媳妇), 女儿冯小妹约14岁。 另外赵氏的儿子小名喜子,24岁。冯嫂丈夫在抗日战争中为新四军从上海通过海上运输时牺牲。 角斜场紧靠东台市新街镇沿海村,不排除三位妇女是那里人的可能性。栟茶、角斜地区没有听说过十分头这个地名,一开始我以为是栟茶东南的六份头,但距离角斜场太远,不大可能。后发现角斜场西北约2.3公里处竟然有十分头,属于东台市新街镇沿海村。十分头从明代清代至民国都属于角斜盐场管理。11纵31旅从北向南打,后勤担架应该在角斜北边。而九分区地方部队从南向北打。卢福祥当时是该旅九十二团九连一排副排长,因此他应该是被新街地区人救了。 如有知道下落者,请联系缪荣株老师,联系。 经查,年2月上中旬,确实发生过著名的“栟北战役”。当时苏中区领导为了打开第一分区和第九分区被隔断的局面,决定在栟茶北边发起一系列战斗,打开封锁线。栟北战役包括2月15~16日的扩展战役,其中就包括攻打旧场(角斜场)。 证据如下: 以下摘自新浪博客竹子的时光庭院 《速读》回忆录样文——卢福祥《亲人》 -08-02 年2月16日,坚持在苏中敌后的我军三十一旅,向占据角斜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以支援与南京、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扬州地区军民反敌清剿斗争。江北的2月,朔风呼啸,滴水成冰。那时,我18岁,在该旅九十二团九连一排任副排长。当晚,奉命率领一排首先破冰泅过20多米宽的河,偷袭歼灭了在范公堤上担任警戒的敌人,抢占了有利地形,为主力部队攻击创造了条件。凛冽的北风,刮得干枯的芦苇深深地弯下腰,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浑身湿漉漉地伏在海堤上,天可真冷啊,刺骨的寒冷,冻得我直打哆嗦……熬到天明,我军向敌人主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立即从地上爬起来,穿着冻得硬梆梆的裤子,步履艰难地和同志们一起,冒着敌人射过来的子弹、炮弹,呐喊着向敌人发起冲锋。当我正在奋力向前奔跑时,突然头被什么东西猛击一下,顿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猛然摔倒在冰冻的田野里……不知过了多久,我苏醒过来,头一阵阵剧痛。“他醒了,终于醒过来了。”我听到一个女人欣喜的声音。我不是在向敌人冲锋吗,这是什么地方呀?想到这儿,我竭力想睁开眼睛,然而,一使劲,头痛得仿佛要裂开,我又昏了过去。蒙眬中,我感觉到有人撬开我的嘴,一股甜润芳芬的汁液,缓缓流入我的口中,顿时,咽喉感到十分惬意和舒服……几天以后,我睁开红肿的双眼,看到床沿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缝补我那件显然已被拆洗过的灰色棉军服。一阵阵婴儿声嘶力竭的啼哭声,使我烦躁、头痛。我默默地想,同志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床沿上的中年妇女看我醒了,连忙起来把我身上棉被掖好,站在床前,爱怜地端详着我,然后,深情地低声问:“饿了吧?”她40岁出头,高高的个子,椭圆型脸上刻着几道皱纹,脑后垂着发髻,上身穿一件藏青棉袄,下身穿一条蓝布棉裤,显得整洁端庄。“嗯。”我确实饿极了,轻轻地点了点头。“不要动,我去弄吃的来。”她边说边向房门外走去,嘴里吆喝着,“喜子家。”听到喊声,一个身材丰满的年轻女子端着碗从门外走进来,笑盈盈地对我说:“小兄弟,趁热喝,娘正在打蛋,待会儿再喝蛋汤。”我确实口渴难捱,贪婪地把那带着一股浓浓芳香的、温甜的汁液,一口口吞下肚……当我心满意足地用舌头舔着唇边残留的汁液时,年轻女子侧着头,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凝视着我,轻声问:“小兄弟,头还疼吗?不用着急,会很快好起来的。”她充满诚挚感情的问候,好比一股暖流汩汩地从我心底流过。又有人推门进屋,嘴里说着:“妈,村长外出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是一个小姑娘清脆的声音。“哦。来,把蛋汤端给那位小哥哥喝。”“好嘞。”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心翼翼地端着热气腾腾的瓷碗走进屋子,她那天真活泼的圆脸上挂着甜甜的笑意。中年妇女也跟着走了进来。看见我床前站着的年龄不相同的三个人,我若有所思地朝她们望过去。中年妇女大概猜出了我的心思,慈祥地指着身旁两人说:“这是我媳妇,叫王秀英;这是我女儿,叫冯小妹;我么……”她停顿一下,“姓赵,孩子她爸姓冯,大家都叫我冯嫂。”她说完,头微微向右歪着,用充满柔情的眼光看着我,好像还在对我说:这就是我们三人的关系,明白了吗?“孩子。”她亲切地称呼我,“坐起来喝吧,趁热喝,这样舒服。”“娘,等一等,让我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喜子媳妇秀英嫂已弯下身,揭开棉被一角,轻轻地把我托了起来,然后,腾出一只手,把枕头揉松,放在床架上,扶我倚靠着。她的这番动作,做得那样大方利索,就像对待亲弟弟一样。就在她贴近我的时候,我的心怦然一动,从她身上传过来一股乳香味,正好这时,我又听到了婴儿啼哭声,难道我喝的是……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我立刻明白了,为了尽力抑制住自己激荡的感情和颤动的身躯,我接过递过来的蛋汤碗,一饮而尽……东头房间又传来婴儿的啼哭声,秀英嫂急忙走了过去。“喜子家,锅里温着面糊,拿去喂,喂饱了,兴许就不哭了。”大娘说。“别是……孩子……生病啦?”我喃喃地说,尽量掩饰心中的不安。“不是生病,是嫂子奶……”小妹朝我眨眨眼睛。霎时,我的双眼湿润了。大娘抱着婴儿进来了,看到我那十分不安的神情,明白了我痛苦的原因,和蔼地伸出手轻轻擦拭我眼角的泪水,安慰我:“小孩子吃几餐面糊糊,不碍事的。好好养伤,早日养好身子,早日归队上阵杀敌。”“怎么啦?”全神贯注喂女儿的秀英嫂听到大娘的话,凑了过来,看到我的神情,她先是感到诧异,瞬间醒悟过来,笑着对我说,“小兄弟,你看,小英子不是好好的嘛,讲身子,我看她比你棒!”秀英嫂的话,惹得大娘、小妹都咯咯地笑了起来。在大娘全家精心照料下,没几天,我的伤势好多了,心情也十分愉快。一天,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唠家常。小妹睁着大眼睛,突然向我发问:“小哥哥,你打仗一定很勇敢,是吗?”“那当然。怕死哪能当解放军!”我显得有些得意和自豪。可惜的是,我的头还在疼痛,不能把话说得更响亮,仍旧靠在床上。“我相信,那天娘把你背回家时,你哼都没哼一声。”小妹把手扬了扬,夸道。“傻丫头,那时,人都快要断气了,哪还能哼哼。”正轻轻拍着怀里小孙女的大娘打断小妹的话。“什么?我差点死掉?”我惊异地问。“嗯。”秀英嫂正在纳鞋底,听到这儿,抬起头,肯定地说,“听娘说,同志们还以为你‘光荣’了,要我们把你抬去掩埋呢!”“把我抬去掩埋!”这更使我感到不解。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大娘讲述了抢救我的经过。“我们部队打角斜场的时候,”大娘侧过头想了想说,“我们村的妇女都参加了前线急救站。仗一开始就打得很凶,炮声炸雷似的轰轰隆隆地响着,枪声像炒豆似的响成一片。那大火啊,把半边天都烧红了。不久,看到了一批一批拱着手、缩着脑袋的俘虏兵押了下来,我们高兴极了。很快,伤员也陆陆续续地抬了下来。我们赶紧忙着给伤员抢救,包扎。“枪炮声还在不远处响着,敌人增援部队来了。能走的伤员都动员自己走,不能走的伤员由部队同志抬的抬、背的背运走了,剩下40多名来不及运走的烈士遗体,部队领导嘱咐我们乡、村干部要迅速组织人员掩埋。当时,太阳快要落山,北风呼呼地刮着,天冷得使人发颤。村长叫我们两人包一个,赶紧把烈士遗体抬去掩埋。你就分给了我。你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满头满脸是血,不知道伤在哪里。看你的样子像是从河里捞出来似的,湿透的棉军装已结成冰,细看你的脸色好像没有完全发白,但你浑身僵硬,没有一点儿反应。我想,兴许真死了,就和另一个大婶准备把你抬去掩埋。可是你的颈脖软软的,头还能转过来垂下去。我一惊,忙说:‘等等!’赶紧把脸贴到你脸上。“‘唉呀!’我惊叫起来,赶忙对一起抬你的那位大婶说,‘没有死,鼻孔里还有微微气息。’我急得忘了对村干部讲,背起你就往家里跑,弄得正在掩埋烈士的乡、村干部莫名其妙,跟在后面喊了好一阵子呢。”“娘把你背回家,我看到你满是血的脑袋耷拉在她肩上,吓得我和小妹都愣了,心想,娘怎么背了个死人回家来!”秀英嫂笑着插话。“还有哩,娘一迈进门槛,连声对我俩嚷着:‘快,快来!帮我把这小同志身上的军装扒下来。’把我们弄得更迷糊。我当时想,娘或许被什么吓着,疯了。”小妹坐在床沿上咯咯地笑着补充道。“当时,我真是着慌发急啊。”大娘接过小妹的话说,“心想,数九天,那么冷,就是好端端的人穿着一身结冰的衣服,时间长了,也会被冻死的,何况你头上还负了重伤。我一发急就把话说乱了,可是要把你那身冻僵的军装脱下来,真难啊……“就说你腿上的绑带吧。由于冰冻成一块,解又解不开,剪又剪不动,实在没办法,我想,救活你要紧,就把你抬到火上烤,才把你身上那套军装扒下来。事后,村长还批评我说:‘冻着的人,不能用火烤,用火烤会把人烤残废的。’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现在看来你总算是闯过来,身子没出什么大问题。“我们替你穿上喜子的单衣,抱上床,用厚厚的棉被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看到你头上裹着一条染着血、沾着土、极脏的急救带,想替你解下来洗洗伤口,换换药。换那条急救带可难死人了!你头上流的血把急救带都染透了,又和你头发粘在一起,冻在一块,没法解,也剪不开,最后,只得一把一把地用热毛巾捂,把冰冻一层一层地化开,才把急救带解下来,直到看到你头顶右侧上有一道食指长的伤口……孩子,那是子弹打的吧!”“可能是。”我下意识地点点头。“对。只有子弹伤,才是那个样子。”大娘肯定了我的判断,接着又说,“我拿把剪刀在火上烧了烧,把你的头发剪光,然后把你的头洗干净,再一摸我那在急救站背着的布兜兜里还有三个急救带,拿出一个把你伤口裹好。孩子,不是大娘新年里说不吉利的话,今后打仗,上阵前,你一定记得剃个和尚头,免得头上负伤增加痛苦。”大娘说完,母女三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她们因救活了我,又看到我一天天康复,感到十分高兴。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眠。北风在屋外一阵阵地呼啸着,远处,大海的咆哮声一阵紧一阵地响着,我听着冯大娘、冯小妹轻轻的打鼾声,心潮起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如果不是大娘细心观察,发现我未死,我已被埋入土中。后来,大娘把我背回家,一家人又想方设法对我进行抢救,精心调养,使我的身体逐渐好起来,但我们之间非亲非故,从不相识,只因我是一名革命战士,她们就如此真诚地救护我,体贴入微地照顾我。是呀,在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军正是由于得到像冯大娘、秀英嫂、小妹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有力的支持,才能生存、发展、壮大,才能战胜强大凶恶的敌人,才能一次次地摆脱险境,走向胜利!啊,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我军的亲人!第二天早晨,当冯大娘又把那芬芳的乳汁端来时,我坚决拒绝喝。然而,她又背着我把它拌入甜面糊里端了回来。不过这次,在她答应下次不再给我喝秀英嫂乳汁后,我才吃下这顿早餐。当时,我正值青春年华,我笃信我会很快康复,重返战场!一天上午,冯大娘在厨房里忙着什么。家庭虽然贫寒,大娘总想方设法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秀英嫂在另一间屋里哼着儿歌,轻轻地拍着爱女。一切显得那么安详、和谐。我请小妹把我搀扶到窗前,发现这是建在海边的一座孤独的三间茅草屋。这时大风已停息,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海滩和零星的盐灶,海边显得有些空旷。一块洼地结着一层厚厚的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亮。西南边有一座村庄,小妹告诉我,那就是十分头村,大娘就是从那里把我背回家的。“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望了一会儿外面的景色,转身问小妹。“我们部队是元宵节那天夜里打仗的,今天是正月二十六。”小妹仰起天真秀气的圆脸回答。“那么,我在这里整整十天啦。”我看到屋檐下堆放着船舵等杂物,问道,“你爹是做什么的?”“爹是船老大,死了三年了。”小妹突然低下了头。“呃,得的什么病?”“不。是替我们部队从上海运东西回来,在海上遇上日本鬼子炮艇,被打死的。”“哦。”我心里一阵难过,她家还是烈属,为支援我军献出过亲人的生命……“喜子哥呢?怎么不在家?”“爹死后,他就上了船。他说,春节期间,上海的东西容易弄到手,运得出来,所以没在家过年。为这,嫂子难过好一阵呢。”小妹答道。“喜子哥多大岁数?”“比嫂子大三岁,过完年是24岁。”我深情地望着她,心想,这也是个经受着种种痛苦、磨难、风险,然而仍然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庭。我今生今世一定要为像大娘家这样的人们摆脱苦难的生活、谋求幸福而奋斗终身,就是战死疆场也在所不惜。突然,一只灰喜鹊从远处飞来,落在门口一棵皂角树上,“喳喳”地叫着,过了一会儿,又拍拍翅膀飞走了,大概是去寻找它的同伴吧!我想我身躯虽痛,四肢无力,但已能站立起来,更主要的是已能行走,因此,也应该寻找我的部队去!“我要去找部队。”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小妹直愣愣地看着我,轻声问:“小哥哥,你要走?”“对,我要走,我要找部队去,我现在就告诉大娘。”由于我坚决要回部队,大娘显得精神恍惚,经常呆呆地站着,心像被苦痛压着。然而,她毕竟是有生活经验的人,她曾经看到过不少因负伤或生病掉队的革命战士,一旦身体稍好,就忍着病痛去找部队,因此,她不像秀英嫂、小妹那样流着泪苦苦地挽留我,而是默默地为我准备路上需要用到的的物品。“大娘,不要难过,仗打赢了,我会来看你的。”我竭力抑制住眼眶中转动的泪水,不让它淌下来。“孩子,你现在这样说,可是一走出这家门,就像鸟儿似的远走高飞了,什么时候顾得上再来看望你大娘呀!”她望着我的眼睛,缓缓地说,低头用袖口擦拭着眼角。天黑了,掌灯时分,我正在整理行装,一个头戴绒帽、身穿短袄的中年男子走进房间。大娘介绍说,这就是他们村的村长。严寒把他冻得不停地跺着脚,揉着鼻子、耳朵,搓着手,看样子他曾来看望过我,此刻,看到我已能起床,学步,感到十分高兴,然而,当他发现我要回部队时,陡感惊讶。不过,在我的坚持下,他答应给我带路,护送我。村长背起大娘为我准备的干粮,我穿上秀英嫂送来的整洁的灰色棉军装和她亲手做的一双蓝布鞋,接过小妹递给我的一根作为手杖的木棍。由于军帽丢失,大娘拿来一顶黑色的绒帽,轻轻地帮我戴上,然后,久久地望着我,深情地问:“还痛吗?”我的心一阵生疼,一时泪如泉涌,嗓门发紧,竟答不上话来……“走吧,孩子。全国解放了,一定要来看望你大娘!”“嗯。”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滚滚热泪从面颊上不断淌下来……夜空,寒星闪烁,海风习习,在海滨旷野的小路上,我和村长走得很远很远了,扭头却还能看到那间孤独的茅屋窗户上射出红色的光亮,像在为我照耀前进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我曾多次寻找冯大娘一家,但始终未找到,连房屋都没有了,这使我感到终生遗憾!真如我三十一旅被敌人重兵包围在如东县海滩上,在情况十分危急时,竟然有一位老渔民趁浓浓的黑夜带领我旅官兵爬海滩,溜过大海汊,脱离险境,全国解放后,军、师领导通过军队、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查找这位老渔民,仍未找到,只在东海之滨流传着“仙人引路”、我军脱险的动人神话故事。呃,军民鱼水情深!那时军民关系多么令人向往、羡慕,终身难忘啊!卢福祥年生,江苏姜堰人。曾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福建省老年书画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军区老战士书画协会会长。今古传奇传媒集团速读杂志社江苏射阳联络站会员。其事迹被收入《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中。寻人启事福建省军区原司令员卢福祥(见《速读》杂志年2月上(总期)第6页《亲人》作者),年9月入伍参加新四军抗日,一生战功卓著。年2月15日在海安角斜场攻坚打援战斗中,年仅18岁的卢福祥在总攻时头部负重伤,被参加前线急救站的烈属、40出头的冯嫂,和她刚生过孩子的21岁的叫“喜子家”的媳妇儿王秀英所救。一个月后伤口基本痊愈,回归部队,继续南征北战。解放后,卢福祥千方百计通过军师领导组织找驻海安的部队和人武部寻找当年海边的救命恩人,但经过地方政府和人武部的努力,包括海安附近的海岛都找遍了,也没有寻查到婆媳的信息。如今,将军已年届90,住在福州干休所里,晚年唯一放不下的心事就是寻找到婆媳俩。知道下落者请联系缪荣株老师,联系。红嫂,您在哪里? 缪荣株 福建省军区,原司令员卢福祥是姜堰区张甸镇人,年9月入伍参加新四军抗日,一生战功卓著。年2月15日在海安角斜场攻坚打援战斗中,任副排长的18岁的卢福祥在总攻时头部负了重伤,血流满面失去了知觉,棉衣结冰僵硬,老百姓都以为他“光荣”了,准备送到后方安葬。 参加前线急救站的烈属、40出头的冯嫂,和她刚生过孩子的21岁的叫“喜子家”的小媳妇儿王秀英负责埋葬。当挖好坑后,王秀英搀遗体的时候,忽然发现卢福祥的鼻孔还微微有点气息,就告诉婆婆。婆婆一看这情况十分惊喜:“这同志还有救呢!”于是婆媳俩将卢福祥抬回家中浆养。好多天,卢福祥只是悠悠地有口气,人还没有醒过来。媳妇儿正在奶孩子期间,也顾不得害羞,救人要紧,情急之中就将自己丰满的乳房乳头塞进卢福祥的嘴里,好,伤员还知道吮吸呢。朦胧中卢福祥感到有人撬开他的嘴,一股甜润芬芳的液汁缓缓地流入他的口内。顿时,他咽喉感到十分惬意和舒服。就这样,媳妇儿将喂孩子的奶,分一半给卢福祥,孩子再另外添加一些粗粮,稀饭。经过一个多星期以后,卢福祥靠乳汁慢慢地清醒过来。当他知道是在群众家里,就挣扎着要找部队去。婆媳俩说什么也不肯。卢福祥清醒了,媳妇儿看到这个18岁的大小伙子再也不好意思给他直接喂奶,就将自己的奶挤进碗里,继续浆养卢福祥。卢福祥回忆的文章中说:“一阵阵婴儿的声嘶力竭的啼哭声,使我烦躁、头疼。我默默地想,同志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的确口渴难挨,贪婪地把那温甜带着一股浓浓芳香的液汁一口口地喝下肚去……当我心满意足地用舌头添着唇边残留的液汁时,她侧着头,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凝视着我。” 一个月后,卢福祥伤口基本痊愈,他要去找部队去。婆媳俩再三挽留他再休养一段时间,他求战心切,最后,经过地方组织上的同意,还是告别了婆媳俩。 回到部队后,卢福祥被纵队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他又南征北战,直到解放后,已经做上了大官。他再也不能忘记那个用乳汁挽救他生命的小媳妇儿和她的婆婆,于是就千方百计地通过军师领导组织找驻海安的部队和人武部寻找当年海边的救命恩人。经过地方政府和人武部的努力,包括海安附近的海岛都找遍了,也没有寻查到婆媳的信息。 在我主编《姜堰名人》时,卢福祥亲笔写来了一篇《亲人》文章,用1万多字详细地叙述了当年的这位红嫂救命之恩和他寻找的过程,总希望有一天突然发现婆媳俩的下落。如今,将军已经快90岁的人了,住在福州干休所里。他的晚年,唯一放不下的心事就是婆媳俩——红嫂,您在哪里? 原载年7月8日《泰州晚报》副刊专栏 以上泰州姜堰学者、领导干部缪荣株转沈小洪。 南沙明远堂文生栟茶沈小洪恳请读者们留言赐教! |
当前位置: 东台市 >寻人启事在角斜场负重伤的原福建省军区
时间:2021/5/2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新街镇迅速传达学习省委和盐城市委东台市
- 下一篇文章: 校园新闻东台市ldquo戏曲进校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